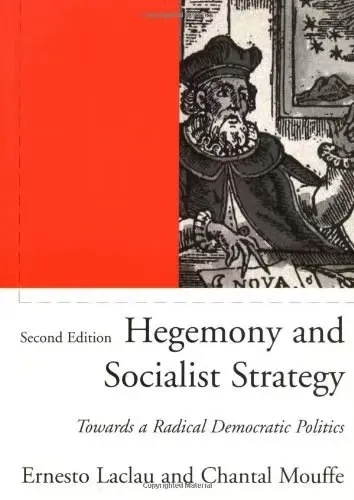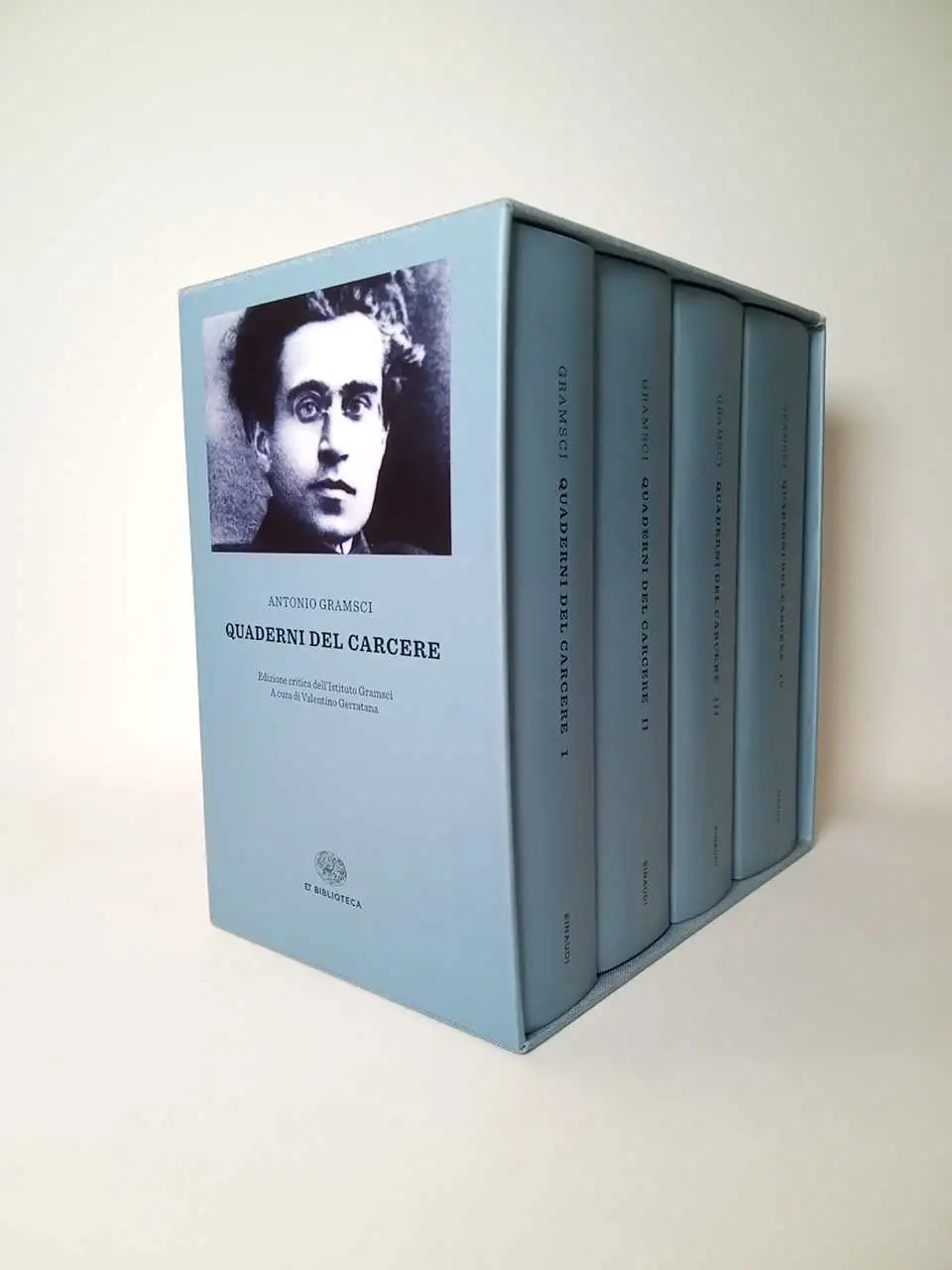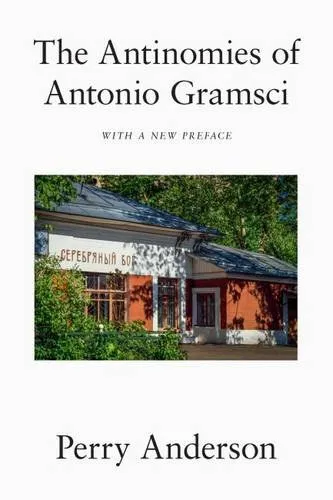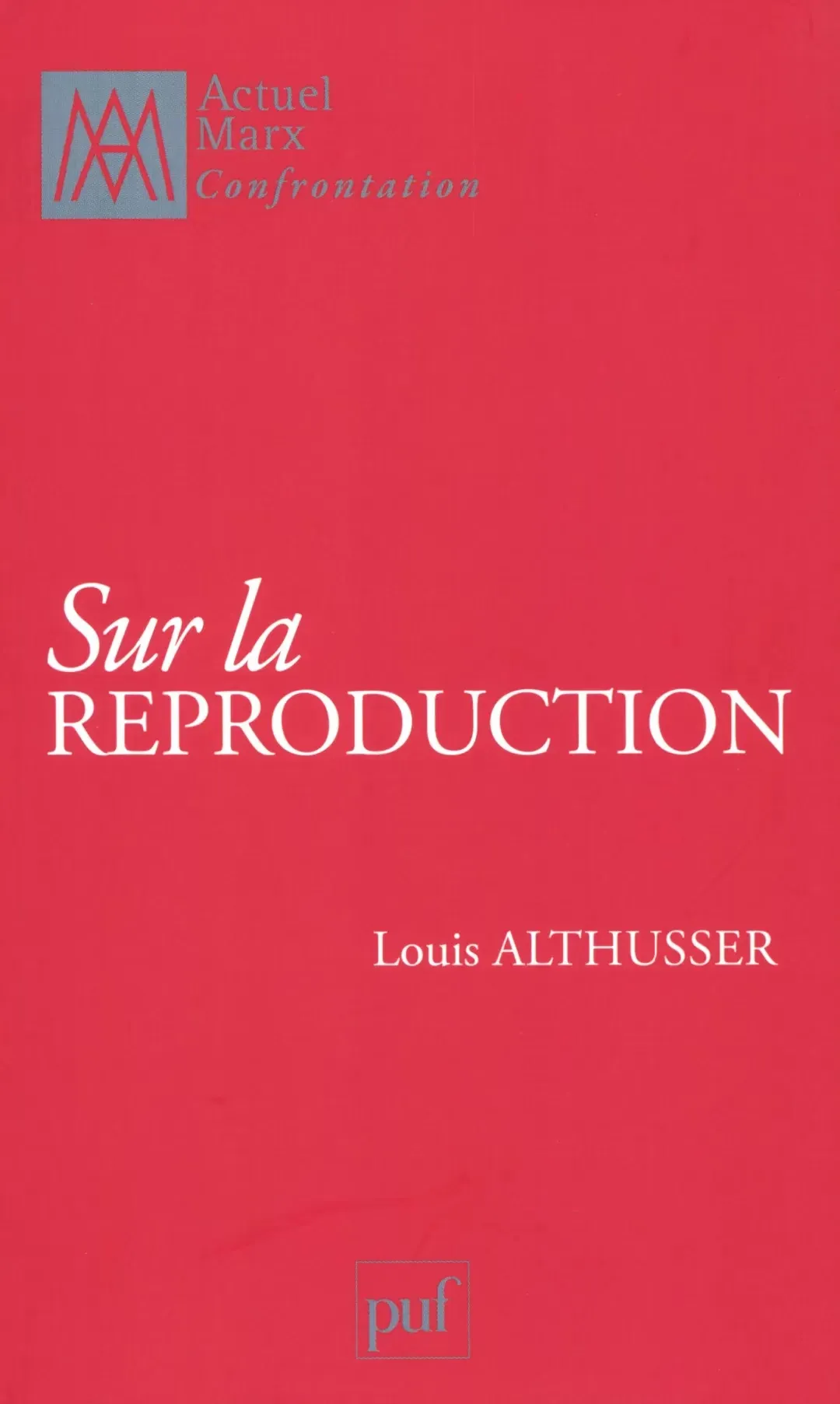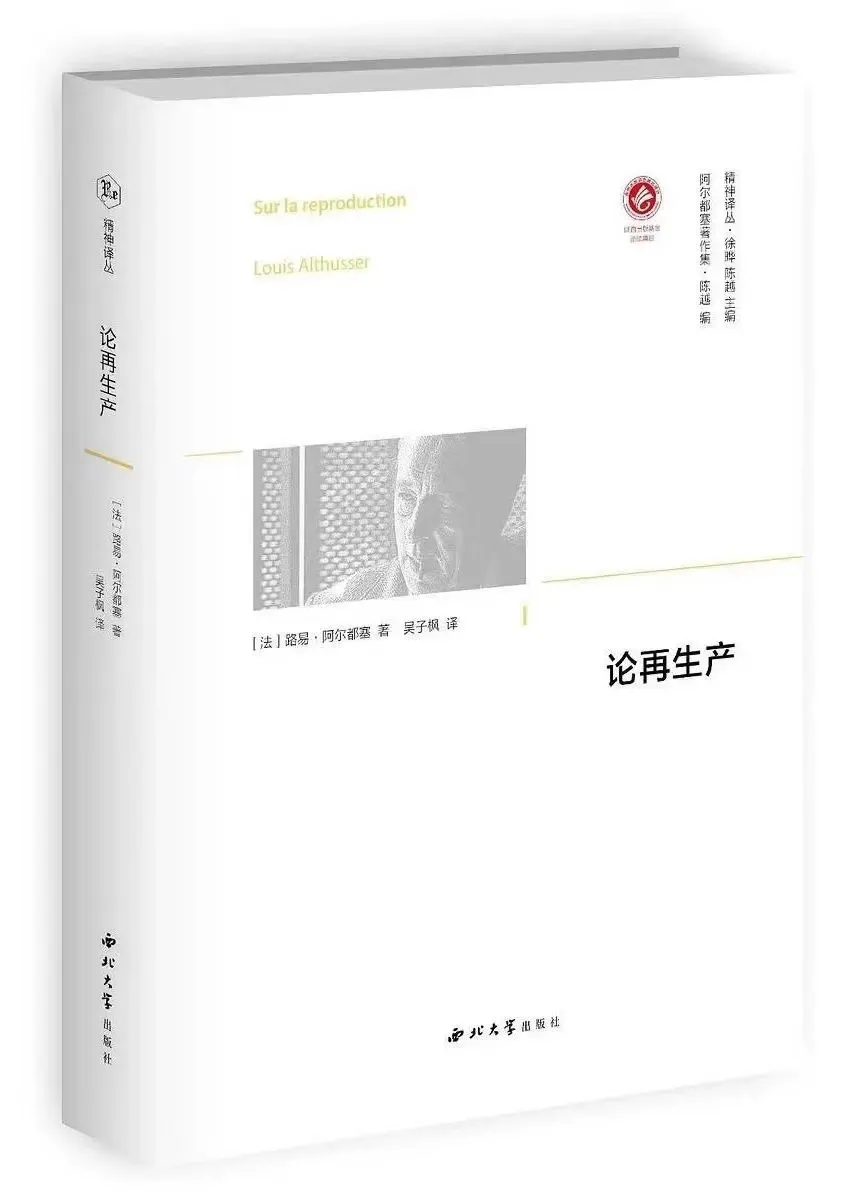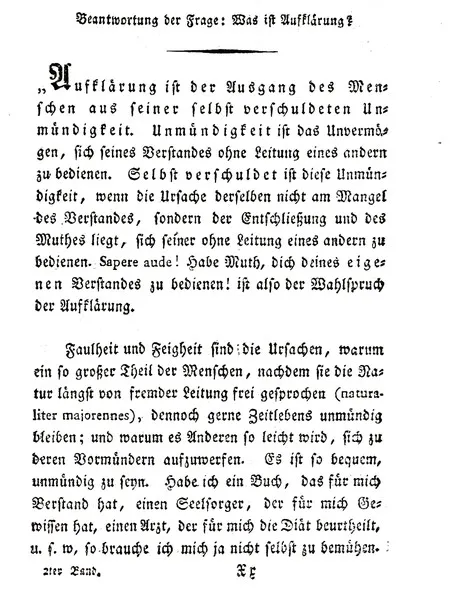陳越|「陣地戰」的話語:葛蘭西領導權理論的再展開
對於以擅長發明概念著稱的葛蘭西來說,「陣地戰」與其說是一個概念,不如說是一種話語。它用隱喻來描述對象,也就是說,用戰爭形式來比喻政治鬥爭形式,因而還只是一種「描述性的理論」[1],具有「前概念的」性質。但正如米歇爾·福柯所說,對這種話語的分析也可以在「前概念的層次上,涉及概念在其中得以共存的場域和該場域所遵循的規則」。在像葛蘭西所夢想的那樣成為一種政治實踐的戰略之前,「陣地戰」首先作為話語實踐的「策略」發揮著功能。

本文原載於《外國文學評論》2024年第3期,獲作者授權轉載。
【編按】兩百多年前,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提到了一類「做那種甜蜜的夢的哲學家們」,他們寄希望於契約和協議,一勞永逸地走向「永久和平」。這個「甜蜜的夢」在今天還是沒有發生任何本質上的變化:它在理論的精巧包裝和過度保護下變得更加觸不可及。
葛蘭西不幸成為「哲學家」們為夢賦予的「保證」之一。尤其是他的「陣地戰」和與之緊密相關的「領導權」概念,被各式來自不同傳統的理論話語挪用、改寫。有人在他的行文中發現了語詞間的「二律背反」;有人把他的概念內涵不斷縮小為己所用;有人則提出新的「游擊戰」戰略將「陣地戰」改頭換面……本文嘗試清掃葛蘭西之後的「哲學家們」為閱讀他設置的重重阻礙,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重新廓清葛蘭西概念的邊界。葛蘭西從未期待過「甜蜜的夢」,這當然不代表他不嚮往和平——相反,葛蘭西深知和平從來不會一蹴而就,人類歷史在締結契約後的短暫和平之外,是無數場大大小小的階級鬥爭。甚至可以說,締結契約本身就是戰爭的另一種形式。歸根到底,對理論新潮的趨之若鶩不能代替「孤獨」地思考,「批判的武器」也不可能取代「武器的批判」。
安東尼奧·葛蘭西用「陣地戰」(guerra di posizione/war of position)來描述爭奪「市民領導權」的鬥爭,而這類鬥爭通常是以意識形態或「文化」對抗的方式進行的——這一點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對於以擅長發明概念著稱的葛蘭西來說,「陣地戰」與其說是一個概念,不如說是一種話語。它用隱喻來描述對象,也就是說,用戰爭形式來比喻政治鬥爭形式,因而還只是一種「描述性的理論」[1],具有「前概念的」性質。但正如米歇爾·福柯所說,對這種話語的分析也可以在「前概念的層次上,涉及概念在其中得以共存的場域和該場域所遵循的規則」[2]。在像葛蘭西所夢想的那樣成為一種政治實踐的戰略之前,「陣地戰」首先作為話語實踐的「策略」發揮著功能。
一、話語的傳統
埃內斯托·拉克勞和尚塔爾·穆夫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戰略:走向激進的民主政治》中談及「陣地戰」時,首先「注意到軍事隱喻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話語中的功能」;也就是說,「陣地戰」固然是葛蘭西的發明,但卻植根於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和理論家善於用戰爭比喻政治的傳統。進而,他們還為這個傳統找到了一個源頭:「從考茨基到列寧,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觀念都依賴於一種想象,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受惠於克勞塞維茨。」[3]
的確,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和理論家向來受惠於克勞塞維茨,而這個「從考茨基到列寧」的名單還可以向兩頭擴展到馬克思、恩格斯和葛蘭西、毛澤東。正如列寧關於「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4]這一「名言」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向公正地把這一論點看做考察任何一場戰爭的意義的理論基礎」。[5]這些政治家和理論家是階級鬥爭(有時直接是武裝鬥爭)和唯物主義的雙重戰士,他們不僅樂於接受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與政治之間的真實聯繫的觀點,而且能夠完全自然地用戰士的感覺和語言器官去咀嚼政治的經驗。戰略、戰術、戰線、陣營、聯盟、武裝、武器、堡壘、先鋒隊、後備軍、消耗戰、殲滅戰、運動戰、陣地戰、包圍、進攻、防禦、退卻……人們不得不承認,這些來自軍事術語的隱喻塑造了馬克思主義政治話語的獨特風格和力量。
然而,假如仔細觀察這類隱喻,就會發現拉克勞和穆夫的說法並不準確:如果前提是克勞塞維茨的著名命題,即「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那麼用政治比喻戰爭才順理成章;如果能夠用戰爭比喻政治,那麼這裡的潛台詞就應該是對這個命題的反轉,也就是說,是因為政治是戰爭的延伸和變形,是戰爭「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以思考戰爭聞名的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承認這個反轉命題「同樣容易理解」。[6]而在他之前,福柯早就建議做出這樣的反轉。[7]這意味著政治——在現存社會中運行的權力關係——「是對在戰爭中表現出來的力量不平衡的認可和延續」;「政治權力的作用應當是通過某種無聲的戰爭,把這種力量對比再一次永遠地記錄下來,在那些制度中、在經濟的不平等中、在語言中,直至在一些人或另一些人的身體中記錄下來」。福柯發現這個「反轉」才是真正的原命題,具有更長久的歷史。按他的說法,這種「把戰爭理解為恆常的社會關係、一切權力關係與權力制度的不可磨滅的根基」的話語——「永久戰爭話語」,作為「與哲學-法律話語相對立的西方第一種全然的歷史-政治話語」,在十六世紀的內戰與宗教戰爭結束之後,就「以一種症狀的方式」出現並盛行於十七至十八世紀英、法等國的政治鬥爭中。福柯沒有忘記指出,正是從這個被他稱作「種族鬥爭話語」的源頭,孕育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概念。[8]
作為高度贊賞克勞塞維茨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列寧在1915年閱讀《戰爭論》時所做的筆記[9]恰恰為我們提供了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將克勞塞維茨命題反轉過來的一個範例。更準確地說,它指出了一條能夠把克勞塞維茨命題和它的反轉命題聯結起來的歷史-邏輯。卡爾·施米特曾把列寧這些簡短的「摘錄、批注、著重號和驚嘆號」稱為「世界史和思想史上最偉大的篇章之一」,理由是這些筆記在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與政治的觀點中更徹底地堅持了戰爭的「絕對敵對性」,因而也更徹底地拒絕了那種把戰爭視同遊戲或賭博的「古典意義」。[10]施米特的理由可以解釋他的政治決斷論,但並沒有抓住列寧思想的重點,也沒有抓住把列寧和克勞塞維茨聯結起來的真正紐帶。在克勞塞維茨那裡,戰爭的絕對敵對性在戰爭性質的「奇怪的三位一體」中「主要同人民有關」(「戰爭中迸發出來的激情必然是在人民中早已存在的」);而現代戰爭之所以驅除了戰爭的「古典意義」,是因為「法國革命突然打開了一個同過去完全不同的戰爭現象的世界」,「戰爭突然又成為人民的事情」。在列寧簡短的摘錄和批注中,二十餘次出現的「人民」一詞緊緊抓住了在這位普魯士軍官意識中起伏著的「盲目」「粗野」「簡單」「自然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才使戰爭「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質,接近其絕對完善的形態」。[11]
雅克·拉康曾說明症狀如何內在於隱喻的結構。簡言之,在替代物(喻體)形成的過程中,被壓抑的東西以另一種方式返回,其剩餘意義便會出現在替代物中。[12]那麼,在構成馬克思主義政治話語的軍事隱喻中得以「返回」的「被壓抑的東西」,不就是在所謂「古典意義」的、作為統治者「遊戲」[13]的政治和戰爭中被貶黜和遺忘的東西——政治的人民性和戰爭的人民性嗎?於是,在列寧的筆記中,我們可以發現,有一條深刻的歷史-邏輯把克勞塞維茨命題和它的反轉命題聯結了起來:只有以「政治是戰爭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個反轉命題為前提,讓戰爭的人民性(絕對敵對性)「返回」政治,使之成為革命的階級政治,才能像列寧那樣「公正地」看待和理解「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個克勞塞維茨命題,讓階級政治的人民性「返回」戰爭,使之成為武裝起來的民族(nation in arms,「全民皆兵」)的人民戰爭。[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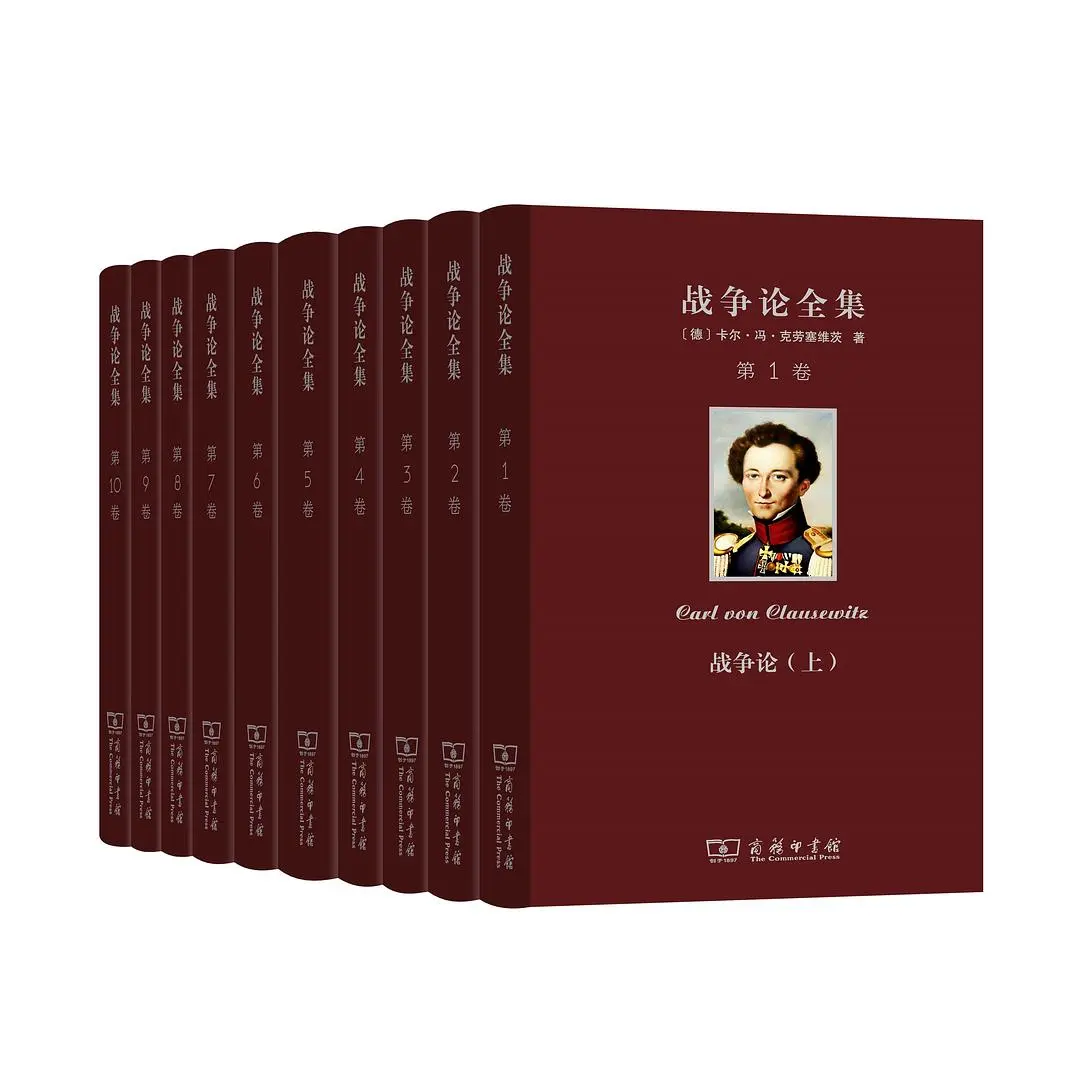
出於對階級政治的退避,拉克勞和穆夫試圖把馬克思主義政治話語中的軍事隱喻傳統與某種「極端軍事主義」的實踐相提並論。然而,這個傳統的真正力量卻來源於:沿著上述歷史-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和理論家喚醒了另一個革命時代的、早已沈睡的、被壓抑的命題,重構了一種貫穿軍事、政治、文化等領域和對象的人民戰爭話語——馬克思主義軍事化政治話語。儘管「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15]。
1857年,馬克思在評論恩格斯《軍隊》一文時寫道:「市民社會的全部歷史非常明顯地概括在軍隊之中。」[16]葛蘭西所說的「‘市民領導權’公式」取代「‘不斷革命’公式」、「陣地戰」取代「運動戰」的時刻,適逢卡爾·波蘭尼描繪的十九世紀「百年和平」達到其頂點並即將走到其盡頭[17];然而桑德拉·哈爾珀琳卻在波蘭尼《大轉型》出版60年後證明,這個關於歐洲工業資本主義和民主制興起與成長的和平神話,只是「一個祛除了血腥衝突、強權與特權、苦難、隔絕和爭鬥的故事」,抹平了帝國主義戰爭、暴力和階級鬥爭的歷史。[18]福柯說:「戰爭,是和平的密碼。」[19]我們可以把這句話翻譯成:戰爭,是市民社會的密碼。
二、一種新的話語
拉克勞和穆夫寫道:「如果在列寧主義中有一種政治的軍事化,那麼在葛蘭西那裡就有一種戰爭的去軍事化。」[20]顯然,他們試圖把「陣地戰」從馬克思主義軍事化政治話語里分離出來,使之轉向他們所鼓吹的「新的政治邏輯」——一種去階級政治的「偶然性的邏輯」。[21]我們只有在說明「陣地戰」話語的真正「新」的性質之後,才能反駁這個觀點。「陣地戰」不是「戰爭的去軍事化」,而是反軍事主義的政治戰。「陣地戰」軍事隱喻的非同尋常之處,在於通過對那個反轉的克勞塞維茨命題中言之未盡的另一些「剩餘意義」的言說,為馬克思主義傳統提供了一種新的、反軍事主義的軍事化政治話語。

我們不妨透過《獄中札記》中的幾段文本來閱讀這種話語:
(1)在軍事戰爭中,戰略目標——消滅敵方軍隊並佔領其領土——一旦達到,和平就到來了。……政治鬥爭遠為複雜:在某種意義上它可以和殖民戰爭或古老的征服戰爭相提並論——在這裡,獲勝的軍隊要永久佔領或打算要永久佔領全部或部分被征服的領土。於是,戰敗的軍隊放下武器,作鳥獸散,但鬥爭卻在政治領域和軍事「準備」領域繼續。[22]
我們從這段文本里可以讀出對那個反轉命題的縮寫:政治是戰爭的繼續。但這個不完整的表述只指出了政治和戰爭的連續性,缺少能夠把政治和戰爭(即便是「殖民戰爭或古老的征服戰爭」)區別開來的要素(命題中的「另一種手段」)。
(2)一個階級佔據統治地位是通過兩種方式,即「領導的(dirigente)」和「統治的(dominante)」。它領導著同盟的階級,統治著敵對的階級。因此,一個階級甚至在取得政權之前,就可以(而且必須)來「領導」;當它掌握了政權,它就佔據了統治地位,但它還要繼續來「領導」……而為了行使政治領導作用(direzione)或領導權(egemonia/hegemony),人們就不應該單獨依賴這種地位所賦予的政權和物質力量。(Quaderni Ⅰ: 41)
這段文本補足了文本(1)中缺少的要素,表述了完整的反轉命題:政治是戰爭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但要注意兩點:第一,它只是以否定的方式補足了這個要素(「為了行使政治領導作用或領導權,人們就不應該單獨依賴這種地位所賦予的政權和物質力量」);第二,它談論的並不是戰爭和政治的區別,而是政治統治地位的兩種方式——「統治的」方式和「領導的」方式(即「領導權」)的區別;準確地說,那種針對敵對階級的「統治的」方式本身就包括戰爭,因而和戰爭一樣表現為暴力的方式,而與之相區別的則是「領導權」,它集中體現了非暴力的方式。正如列寧把克勞塞維茨命題中的「另一種手段」定義為「暴力手段」[23],這段文本實際上以否定的方式把反轉命題中的「另一種手段」定義為非暴力的[24]。然而問題在於:這裡的「另一種手段」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這便是上述命題中言之未盡的「剩餘意義」。只要這種意義尚未得到肯定的表述,「另一種手段」沒有被明確地規定,葛蘭西的全部理論努力就會落空:他使政治得以區別於戰爭(暴力)的那個「領導權」就面臨著淪為一個空洞的、烏托邦式的政治理念的危險,這種危險由於後文將提及的另一些原因始終存在著;因而他也無法使馬克思主義軍事化政治話語擺脫「軍事主義」的誘惑,這種誘惑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實踐的歷史中也始終存在著。因此,這種「剩餘意義」必須為自己找到一種新的話語——
(3)1870年以後的時期,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國家內部和國際的組織關係變得更加複雜而龐大,四八年的「不斷革命」公式在政治科學中被「市民領導權」公式所擴充和超越。同樣的事情就像發生在軍事藝術中一樣,也發生在政治藝術中:運動戰日益轉變為陣地戰,而且可以說,一個國家和平時期對戰爭的技術準備越是細緻入微,它就越能贏得戰爭。現代民主制的龐大結構,不但作為國家組織,而且作為市民生活的結社綜合體,就政治藝術而言,儼然構成了陣地戰前線的「塹壕」和永久性城防工事:它們把從前一直是戰爭「整體」的運動要素變成了僅僅是「局部的」東西。(Quaderni Ⅲ: 1566-1567)
葛蘭西把國家比喻為陣地戰中的「前方塹壕」,背後是市民社會的「一系列堅固的堡壘和營盤」(Quaderni Ⅱ: 866),又說「市民社會的上層建築就像現代戰爭的塹壕體系。在戰爭中,猛烈的炮火有時看似摧毀了敵人的整個防禦體系,其實只不過摧毀了他們的外層防線[按:指國家]」(Quaderni Ⅲ: 1615)。陣地戰就是塹壕戰,葛蘭西把「現代民主制的龐大結構」理解為「國家組織」和「市民生活的結社綜合體」的共同發展,但對於國家在「塹壕體系」中扮演的角色,他的比喻有些捉襟見肘,而市民社會則佔據了「陣地戰」中心地位。在文本(3)稍後的另一則筆記中,葛蘭西批判自由主義經濟學說「是以一種理論錯誤為基礎的……也就是說,它是以政治社會[按:指國家]與市民社會兩者的區分為基礎的——這原本只是方法上的區分,現在卻儼然作為有機體的區分被提了出來」(Quaderni Ⅲ: 1590)。但我們看到,正是以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為基礎,葛蘭西提出了「陣地戰」的話語。
我們需要暫時放過葛蘭西的這些含混和矛盾,來理解「陣地戰」話語的「新」的性質。這種話語之所以是新的,是因為它對「另一種手段」作出定義的理論依據已經不是在戰爭和政治之間加以辨析的概念差異,而是在「不斷革命」和「市民領導權」這兩個「公式」之間、在突然發動正面進攻奪取國家政權的「運動戰」和在市民社會開闢長期戰場的「陣地戰」之間、被1848—1871—1917這些年份[25]及其所對應的空間徹底拉開了的歷史距離。
既然「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工具」[26],那麼戰爭和政治的概念差異也就在包含戰爭工具在內的政治本身中「繼續」存在,並表現為葛蘭西思考的一系列二元對立:「統治的」與「領導的」、「野獸性與人性、武力與同意、權威與領導權、暴力與文明」(Quaderni Ⅲ: 1576)……這些二元對立無不來自悠久的政治觀念史傳統(從馬基雅維利到列寧),屬於「政治社會學的普遍公理」[27]。然而,當葛蘭西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加入這個系列時,儘管它同樣不是葛蘭西的發明,甚至還帶著「理論錯誤」的風險,我們卻看到了一個真正的理論創新——這便是「市民社會」與「領導權」的聯結(他稱之為「‘市民領導權’公式」),以及從這個「公式」里誕生的「陣地戰」話語。
一方面,正是由於與「市民社會」的聯結,「領導權」這個來自俄國革命和第三國際的觀念獲得了新的意義,它的「難題性(problematic)從東方無產階級的社會聯盟向西方資產階級權力的結構偏移」(《葛》:37)。對「市民社會」的援引可以幫助葛蘭西「在西方」去展開他認為列寧在「統一戰線」中已經「懂得」卻「沒有時間展開」的公式:「它要求偵察地形,並且識別出由市民社會要素所代表的那些塹壕和堡壘的要素。」(Quaderni Ⅱ: 866)這些「要素」反映了資產階級社會權力關係的新變化——對「強制」與「同意」的重新分工和配置,也意味著工人階級和民眾的反抗鬥爭需要採納的新方式。馬克思主義傳統一向重視對十九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統治形式(尤其是波拿巴主義、沙皇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鎮壓性國家機器)的理論和戰略思考,但發達資本主義民主制政體的權力關係的新穎性在葛蘭西這裡才「第一次發展成為一個統帥性的主題」(《葛》:40)。誠如佩里·安德森所說:「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如此集中地關注了西歐議會制度的同意合法性這個迄今為止一直被回避的問題——是孤獨且重大的。」(《葛》:69)
另一方面,正是由於與「領導權」的聯結,「市民社會」從以資產階級財產關係和物質交往為核心的社會關係中獲得了它在資產階級權力結構中的新的地位:意識形態機器的地位(被葛蘭西稱為「市民社會的上層建築」[Quaderni Ⅲ: 1615])。這種地位的改變本身是資產階級領導權鬥爭的歷史果實——資產階級思想家早就在「理性的公開運用」的旗幟下把這個原本是私人關係的領域構想為一種資產階級公共權力的運用的領域了。[28]但這也就意味著,與列寧在軍事鬥爭和武裝的政治鬥爭中正確地堅持並勝利地運用的「秘密性」原則[29]不同,「市民社會」的領導權鬥爭需要在「公開」的條件下進行,需要像馬克思那樣從對手手裡接過「批判的武器」並把它改造成「更精良、更準確無誤的意識形態武器」(Quaderni Ⅱ: 1509),需要「在漫長、困難、充滿矛盾、前進和倒退的過程中」(Quaderni Ⅱ: 1386)培養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作為戰士,需要對對手「採取批判-爭辯而非教條的態度」(Quaderni Ⅲ: 1863),需要以建立新的「高級文化」為戰鬥的目標[30],因為只有這種文化才能同「有教養的階級的意識形態進行鬥爭」(Quaderni Ⅲ: 1858),從而把鬥爭提高到領導權的階段,而這一切都「需要耐心和創造精神方面的非凡品質」(Quaderni Ⅱ: 802)……所有這些論點都一遍遍寫在葛蘭西的筆記中,描繪著一種新的鬥爭方式,與馬克思主義者在軍事鬥爭和武裝的政治鬥爭中熟練運用的那些方式完全不同。
於是,「市民社會」與「領導權」的聯結,以及在這一聯結中形成的主題和論點,都被統攝在「陣地戰」話語中。[31]一個「陣地」並不先於戰鬥而存在,甚至並不先於佔領而存在,因為一個沒有佔領的陣地就是屬於對手的,一個沒有永久佔領的陣地就是潛在地屬於對手的;而這個陣地的戰略價值,也取決於對手所建立的「堅固的堡壘和營盤」。因此,「陣地戰」最根本的特徵是在對手的地盤上戰鬥。與以打碎舊的鎮壓性國家機器為目標的「運動戰」不同的是,佔領陣地是為了保留並改造它,把它轉變並確立為自己的戰鬥「立場」。雙方的陣地犬牙交錯,不斷的佔領意味著陣線的重新劃分和推進以及力量對比的改變,而全面的佔領才是最後的勝利。
葛蘭西在最初的筆記中就曾經提醒:「應當記住這個總的標準:如果要在軍事藝術與政治之間作出比較,就要始終帶一點保留——換言之,是作為對思考的刺激,或者作為一種反證法的說法。」(Quaderni Ⅰ: 120)政治與戰爭的真正深刻的聯繫並不在於字面的相似性,不記住這個「總的標準」,就會滑向軍事主義。正如列寧依據克勞塞維茨觀點對軍事主義觀念的諷刺:「表象究竟還不是現實。戰爭愈是政治的,看來就愈是軍事的;戰爭愈缺少政治的成分,看來就愈顯得是‘政治的’。」[32]「陣地戰」話語的悖論在於:通過用軍事隱喻談論政治,葛蘭西恰恰提供了一種反軍事主義的政治話語,揭示了領導權鬥爭與一般「政治和軍事鬥爭」的區別——
人們產生了錯覺,以為在意識形態戰線和政治-軍事戰線之間還存在著(不止於形式和隱喻上的)其他的相似性。在政治和軍事鬥爭中,從抵抗最薄弱的部位取得突破,以便能夠用正是由於消滅了較弱的側翼而獲得的最大限度的力量去攻擊最強的部位,這可能是正確的戰術……然而,在意識形態戰線,打敗側翼之敵和搖旗吶喊之輩卻幾乎談不上任何重要性。在這裡,你必須和最傑出的對手交鋒。……當一門新的科學表明自己有能力面對那些具有對立傾向的偉大戰士,當它要麼用自己的手段解決了他們所提出的至關重要的問題,要麼以斷然的方式表明這些問題都是些假問題,這時它才證明瞭自己的有效性和生命力。(Quaderni Ⅱ: 1423)
三、方法的啓示
在提出1870年以後從「‘不斷革命’公式」向「‘市民領導權’公式」、從「運動戰」向「陣地戰」轉變的命題之後,葛蘭西在相隔幾頁的另一則筆記中,借由對歷史局勢進行分析的「方法論標準」的討論,說明瞭他先前提出這個命題的理由:
事實上,只有到了1870—1871年,由於巴黎公社的嘗試,1789年的全部胚芽才在歷史中枯竭;這時,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新階級不僅戰勝了不甘承認自己已被徹底取代的舊社會的代表,而且戰勝了斷定1789年革命創立的新結構也已經過時的那些甚至更新的集團,從而不僅向舊階級,而且向更新的階級證明瞭自己的生命力。進而,從1789年的實踐中誕生、1848年前後在意識形態上得到發展的政治戰略與戰術的全部原則[按:指「不斷革命」公式或運動戰]都在1870—1871年失效了。(Quaderni Ⅲ: 1581-1582)
我們可以從這段表述過於簡略的文本里提取出三個要點: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中為無產階級提出的「不斷革命」公式,本身依賴於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和經驗;二、巴黎公社的鬥爭和失敗意味著資產階級革命性的「枯竭」,資產階級成為反動的統治階級;三、「不斷革命」為資產階級帶來統治地位之日,也是它在無產階級那裡失效之時。
雅克·泰克西埃注意到這段文本與恩格斯去世前不久寫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在表述上有驚人的相似性。[33]在那份著名的「政治遺囑」中,恩格斯談到他和馬克思在當時提出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和步驟的觀念」多麼依賴於法國大革命的「經驗」和「榜樣」;談到這場「少數人的革命」造就了新的統治階級,而正是巴黎公社「結束了這個時期」;談到「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34]更令人感興趣的是,作為軍事理論家的恩格斯在長篇論證「舊式的起義,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築壘巷戰,現在大大過時了」之前,在一個簡短的句子里使用了陣地戰的隱喻:「既然連這支強大的無產階級大軍也還沒有達到目的,既然它還遠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擊取得勝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鬥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那麼這就徹底證明瞭,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實現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35]
葛蘭西在他的筆記里從未引用過恩格斯的這篇文章,但除了對這一點表示疑惑或好奇,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兩者在明顯的相似性之外的差異。恩格斯關注的是具體的戰略轉變,如利用普選權進行長期鬥爭和放棄街壘戰;而葛蘭西則側重於為戰略轉變提供一個更具方法論意義的論點(不要忘了「方法論」是那則筆記的主要話題)——它隱含在上述文本三個要點的聯繫之中。我們在葛蘭西最初的筆記里找到的一小段話正好可以用來佐證和概括這個彌足珍貴的論點:「還要記住一點:在政治鬥爭中不要模仿統治階級的鬥爭方法,否則容易中埋伏。在當前的鬥爭中,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Quaderni Ⅰ: 121)
換言之,以不模仿統治階級的方法為方法。在深入理解這個論點之前,我們先要搞清楚:究竟是什麼使得「不斷革命」公式和運動戰失效、使得這種方法不能再被模仿了呢?用葛蘭西的話說,一方面是資產階級革命性的「枯竭」——它作為革命階級死掉了;另一方面是它在反對和鎮壓新舊敵對階級的鬥爭中「證明瞭自己的生命力」——它作為統治階級強大了。一言以蔽之,就是資產階級統治的領導權的確立。
這裡的「領導權」,我們是在葛蘭西所說的「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即披著強制的鎧甲的領導權」(Quaderni Ⅱ: 763-764)以及「市民社會與國家同一」(Quaderni Ⅲ: 1590)的意義上使用的。安德森和阿爾都塞先後分析和批評過葛蘭西在「領導權」定義和用法上的「變異」與「矛盾」:它們使這個概念「過度擴展」或「膨脹」,以至於有可能淪為一個空洞的政治理念(詳見《葛》:37-60)[36]。實際上,產生這些「變異」和「矛盾」的根源,在於葛蘭西無法冒著他曾經指出的「理論錯誤」的風險,一以貫之地以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為基礎來認識現實。他看到「在現今經典的議會制政體領域,領導權的‘規範’運用的特點,在於武力與同意的結合,兩者的相互平衡」(Quaderni Ⅲ: 1638)。這種「結合」打破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而這種「平衡」則凸顯了「西方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不對稱:強制位於其中之一,同意則位於兩者」(《葛》:63),也就是說,國家壟斷著暴力,卻與市民社會分享著意識形態權力。就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客觀結構生產著商品拜物教的「虛幻形式」[37]那樣,這種資產階級權力關係的客觀結構也生產著資本主義社會可以通過無需暴力的同意進行自治的虛幻形式——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就是這樣的虛幻形式。
葛蘭西之所以要從這種虛幻形式出發去達到他的理論創新,是因為「市民社會」的路標至少可以幫助他認識資產階級權力關係的新變化:隨著「現代民主制的龐大結構」的建立,尤其是「大型群眾性政黨和大型經濟工會」(Quaderni Ⅲ: 1566-1567)的興起,「國家應該被理解為不僅是政府機器,而且也是‘私人的’領導權機器或市民社會」(QuaderniⅡ: 801)。阿爾都塞後來就是沿著這條「以前只有葛蘭西一個人有所涉足」的道路前進,正確地指出了國家既存在於「(鎮壓性)國家機器」中,也存在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38]換言之,在資產階級國家權力內部存在著一種被葛蘭西稱之為「分權」的關係,即意識形態權力與存在於鎮壓性機器中的那部分政治權力(狹義的「政權」)的相對分離:屬於「市民社會的上層建築」的那些「機器」、機構,以及在其中生活、「交往」和「運用理性」的知識分子,分享了「絕大部分」意識形態權力[39],從而打破了原先意識形態權力與政權之間的單一的直接依附關係。在葛蘭西看來,這種體現著「克羅齊所謂‘永恆的政教衝突’[按:即‘國家與教會的衝突’]」的新型「分權」,構成了比「三權分立」更根本的資產階級權力關係(see Quaderni Ⅱ: 751)。這就是葛蘭西認識到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沒有為他提供「分權」的正確分界線,但市民社會內在於國家的存在和發展卻構成了「分權」的條件。
意識形態權力與政權的相對分離,相當於康德對「服從」的領域與「理性的公開運用」的領域的劃分[40],意味著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之後建立的資產階級領導權的嶄新形式。相對分離的兩種權力形成了一種並非單一肯定性的、「批判的」關係,我們不妨把這種關係中的意識形態權力稱作一種「批判的權力」,以便與康德把政權稱作一種「擁有權力的批判」[41]相對應。「批判」通過總是分櫱出新的對立立場的鏡像形式,建立了一個需要不斷在辯證的歷險中重新試探自身限度的「批判理性」、一個必然超越特定「質料價值」的高度形式化的意識形態空間、一個一貫通過各種「反體系運動」拓展其疆域的領導權體系。無數的「主義」和立場之爭,彼此都具有一種「像配偶關係那樣的對子關係」[42],每一方的立場都被另一方的立場預先規定,卻沒有任何一方具有佔領、消滅另一方的意志和能力。實際上,它們是被同一種遊戲規則——市民社會的規則(「運用理性吧……但是要服從!」[43])——預先規定了。[44]這種被稱作「批判」的協議或共謀關係規定了意識形態權力與政權相對分離的限度,它改變了階級統治的形式,反映了階級統治基礎的擴大,但絲毫不改變統治的階級性質。
有趣的是,作為對這種意識形態戰爭狀態——同樣是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沈思的結果,在當代瀰漫著一種新的話語:一種軍事化哲學話語。游擊戰,這種原本在現代人民戰爭中獲得成功運用的戰術形式,被「委以哲學使命」,「以新的世界精神的形象出現」了。[45]施米特的「游擊隊理論」、德·塞托的「戰術」、德勒茲和加塔利的「遊牧戰爭機器」、哈特和奈格里的「網絡式鬥爭」,逐一成為這種「世界精神」的理論化身。[46]這種話語的特點,在於用「政治神學」「符號學」「遊牧學」或「蜂群智能」的語言,抽空了對具體現實的歷史鬥爭質料的具體分析,把戰爭的絕對敵對性形式化了——這裡只有與人為敵的慾望-能指,而沒有戰勝和消滅敵人的意志和能力——而形式化正是構成遊戲的條件。如果說「古典意義」的政治和戰爭是統治者的「遊戲」,那麼這種當代意識形態的「游擊戰」就是被統治者的遊戲,「是一門弱者的藝術」[47]。這種「游擊戰」話語就像德勒茲和加塔利所贊頌的德國劇作家克萊斯特那樣,「歌頌著一部戰爭機器,並在一場事先已經失敗的戰鬥中以這部機器來反抗國家機器」[48]。葛蘭西早就思考過這一點:
個人(即使作為廣大群眾的組成部分)本能地傾向於認為戰爭就是「游擊戰」或「加里波第式戰爭」(這是「游擊戰」的一種高級形式)。在政治中犯這樣的錯誤,是因為沒有正確理解什麼是國家(其完整意義是:專政+領導權)。(Quaderni Ⅱ: 810-811)
在《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中,詹姆斯·C.斯科特宣稱「對農民而言,最合適的[反抗]形式就是廣泛的游擊式的消耗戰」——「行動拖沓,假裝糊塗,虛假順從,小偷小摸,裝傻賣呆,誹謗,縱火,破壞等等」。[49]這可以說是為德勒茲和加塔利所謂「游擊戰明確地以非戰鬥為目的」[50]提供了注腳。因此,拉克勞和穆夫鼓吹「陣地戰」是「戰爭的去軍事化」,實際上為我們展示了一條從「陣地戰」向「游擊戰」蛻變的道路。他們誇大了「陣地戰」在葛蘭西那裡作為「文明的不斷解體」和「建構」的意義,以此來消解這種軍事話語中包含著的戰爭的絕對敵對性,把陣地的佔領解釋為「身份的持續變化」,從而擯棄階級政治這個「葛蘭西思想內部的本質主義內核」。[51]
葛蘭西的認識與這種解釋正好相反。他說:「任何政治鬥爭都總是具有一種軍事底色。」(Quaderni Ⅰ: 123)更重要的是,他並沒有忘記自己說過的「如果要在軍事藝術與政治之間作出比較,就要始終帶一點保留」這個「總的標準」,也就是說,他並沒有用戰場上戰術的簡單轉換來代替政治的戰略思考,從而「把‘陣地戰’和‘運動戰’簡單對立起來」[52]:「在政治上,只要問題在於贏得的那些陣地還不是決定性的,運動戰就會繼續存在,這樣才能使全部領導權的和國家的資源無法被調動起來。」(Quaderni Ⅱ: 802)這句話可以引起不同的解讀,但在邏輯上毫無疑問地意味著:決定性的勝利只能屬於「陣地戰」和「運動戰」的同時完成,放棄市民社會的佔領國家和放棄國家的佔領市民社會,都是要失敗的。
事實上,一旦與反對統治階級國家的「運動戰」相脫離,「陣地戰」就會向這種從「個人」(或以個人為中心的「諸眾」)出發的「游擊戰」蛻變,而這種「游擊戰」只能是「弱者的藝術」或「武器」。在當代,這種普遍的傾向是以「市民社會」的遊戲規則為前提,以「模仿統治階級的鬥爭方法」為代價的。因為從根本上說,統治階級為創造和保障階級剝削的條件而進行的鬥爭,一開始就不僅在力量上、而且在規則上支配著被統治者的反抗鬥爭,兩者是不同步、不同質的,也是不對等的。被統治階級一般需要經歷長時間伴隨著失敗和挫折的摸索,才能找到從這種被支配狀態下解放出來的、屬於自己的鬥爭方法。
當政治和戰爭都還是統治者「遊戲」的時代,一個名叫馬基雅維利的人曾無情地打破這種狀態,發現了從中解放出來的「方法」。儘管這個人曾寫過一部《戰爭的藝術》,反對貴族騎兵在戰爭中的優先性,並且試圖建立佛羅倫薩共和國的人民軍隊,但只有寫下一則又一則關於馬基雅維利的筆記的葛蘭西,以及後來寫下《馬基雅維利和我們》的阿爾都塞,才揭示出他作為意識形態戰場上的陣地戰大師的面目:「馬基雅維利很少說出來卻總是在實踐的方法的准則,就是必須思考到極端。這意味著在一個立場/陣地中思考,在那裡提出一些極限的論點,在那裡,為了使思想成為可能,就需要佔據一個「不可能之物」的位置。」阿爾都塞接著解釋說,對馬基雅維利而言,這個「不可能之物」(「新君主」)意味著告誡意大利人民「不必依賴任何東西,既不依賴現有的君主,也不依賴現有的國家」[53]——歸根到底,就是不依賴「統治階級的鬥爭方法」。
餘論:一點「剩餘意義」
本文有意把一個話題放到最後來討論。不討論它,我們對「陣地戰」話語的認識不僅是不完整的,而且忘掉了這種話語賴以提出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葛蘭西需要依靠「對比俄國和西方這兩個地緣政治劇場中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葛》:10),才能正當地提出這種話語:
在東方,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是原始而凍結的;在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存在恰當的關係,國家一旦動搖,市民社會堅固的結構就會立即顯露出來。國家不過是一道前方塹壕,它背後屹立著一系列堅固的堡壘和營盤……(Quaderni Ⅱ: 866)
借用拉康的說法,可以認為在葛蘭西的隱喻里同樣包含著一種「壓抑」機制:在第三國際語境中,一種不同於俄國革命道路的西方社會主義新戰略的提出,自然需要以承認前者的正當性為前提。我們還應注意,在葛蘭西的一系列二元對立中,「東方」與「西方」的加入是成問題的:構成「陣地戰」理論創新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實際上只屬於「西方」。正因如此,葛蘭西也不能像在其他二元對立中那樣,去談論「東方」/「西方」兩個對立面的「結合」或「同一」——其他的對立都是共時性的,而這組對立更像是歷時性的,因為它看上去不是由地理的距離而是由歷史的差距造成的。在後來的筆記中,葛蘭西索性使用「落後國家」(paesi arretrati)與「現代國家」(Stati moderni)(see Quaderni Ⅲ: 1567)或「最先進國家」(Stati piú avanzati)(see Quaderni Ⅲ: 1615)來代替「東方」與「西方」。

這裡隱含著危險的推論:如果說葛蘭西放棄了「在東方」(至少在其「落後」情況下)運用「陣地戰」的設想——他直言「這個問題在現代國家才存在,落後國家或殖民地則不然」(Quaderni Ⅲ: 1567)——那麼是否意味著在那裡必須以市民社會的發展為前提,等待這種發展完成之後才能運用「陣地戰」呢?葛蘭西是否也像列寧諷刺過的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全體英雄們」一樣,眼裡只看到「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道路」呢?[54]
葛蘭西在1917年12月為贊美十月革命而寫的那篇著名的《反〈資本論〉的革命》,可以向我們證明在他的意識里從未給這種經濟決定論的進化論留下地盤。儘管他最終求助於「人的意志」的能動性[55]來解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但仍然在不經意間說出了更深刻的東西:「現在,受著社會主義教育的俄國無產階級,將要在英國今天已經達到的最高水平上開始自己的歷史。既然它必須從零起步,它就將在別處、從已經改善了的地方起步……」[56]
俄國無產階級之所以能夠「在別處」「從零起步」,正是因為列寧所說的「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和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57]。這個「別處」意味著,「落後」與「先進」或「東方」與「西方」的關係,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坐標中並不是歷時性的,而是共時性的;它們不是按照歷史進化論的原理,而是按照歷史的不平衡發展的原理聯繫起來的。在不平衡發展的原理中,歷史並不等待「落後」者。T.S.艾略特睿智地說過,藝術並不進步,但它會複雜化。[58]歷史也是這樣,它並不在庸俗進化論的意義上「進步」,但它會把一切東西,新的和舊的,「先進」和「落後」,捲入一個越來越複雜的發展的體系(就像列寧說的「總漩渦」[59]),並在這個體系中製造矛盾的「最薄弱環節」[60]。可以說,列寧正是利用這個原理在1917年的俄國(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區域)取得了「運動戰」的勝利;而如果聯想到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同樣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區域)為什麼和青年黑格爾派分道揚鑣並走向無產階級革命,我們就會立刻明白:這個原理也是馬克思思想的起點。
但我們何嘗不可以說,歷史也是利用了這個原理,在十月革命七十多年後的蘇聯(作為「市民社會」發展的「落後」區域)製造了「陣地戰」的失敗呢?讓晚年的列寧在他的「政治遺囑」中顯得憂心忡忡的,正是這場剛剛開始的戰鬥:「……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種根本的改變表現在: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現在,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61]我們還應指出,列寧的這個「文化革命」與葛蘭西提出的「知識與道德改革」[62](借用了歐內斯特·勒南的說法)具有同等的政治戰略內涵。
只有把「東方」「西方」的對立放回到共時性的、不平衡發展的體系中,才能使葛蘭西為了「在西方」提出他的戰略而刻意壓抑的東西「返回」到「陣地戰」的話語中,以便重新發現其作為「剩餘意義」的力量。在這個不平衡發展的體系中,正如葛蘭西告訴我們的那樣,從距今一個半世紀前的某個時刻起,歷史就打破了以後的人們依靠建立和發展市民社會來爭取自由的啓蒙主義夢想。市民社會從一個革命階級的武器,變成了一個統治階級的權杖,成為資產階級領導權的工具和象徵。對這個體系中的所有人來說,它從一開始就是作為資產階級統治權力的一部分、作為「統治階級的鬥爭方法」而被給予的。例如,在當今世界的許多地方出現的、以「市民社會」名義進行的鬥爭,實際上總是隱含著對某個領導權霸權國家或體系的深刻的「從屬關係和經濟上的被奴役」——葛蘭西很早就指出了這一點(see Quaderni Ⅲ: 1562)。
因此,葛蘭西在囹圄之中為我們貢獻的真正有力量的思想——「陣地戰」話語的核心理論功能,就是把「陣地戰」作為市民社會本身的前提,而非相反。只有把市民社會開闢為「陣地戰」的戰場,才能利用其「和平的密碼」,破解其遊戲的規則,分化和限制其權力,與之鬥爭和周旋,直至把它引向革命的政治。這不再是「少數人的革命」,如列寧所說,「只有根據地球上絕大多數人口終於在資本主義本身的訓練和培養下起來鬥爭了這一點,才能預見到鬥爭的結局」[63]。
注釋:
[1] 路易·阿爾都塞在論及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地形學隱喻和國家理論中的「機器」隱喻時指出,這類「隱喻性的……仍然是描述性的理論」既是偉大科學發現的開端,又有不穩定性的缺點,面臨阻礙理論發展的風險,因而需要「把描述性的理論發展為理論本身」(詳見路易·阿爾都塞《論再生產》,吳子楓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66-170、449-451頁)。對於「陣地戰」隱喻,我們也可以作如是觀。
[2] 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李沅洳譯,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3年,第105頁。譯文據原文有所改動(see Michel Foucault, OEuvres, Ⅱ,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2015, p.64)。
[3]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2014, p. 60.
[4] 原文為「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詳見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1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43頁)。
[5] 詳見列寧《社會主義與戰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對戰爭的態度)》,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7頁。
[6] 詳見邁克爾·沃爾澤《論戰爭》,任輝獻、段鳴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頁。
[7] 福柯先是在《監視與懲罰》(1975年)中提及這一看法,隨後在1976年的課程《「必須保衛社會」》中詳加論述。
[8] 詳見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社會》(中譯本不恰當地刪去了原標題帶有的引號),錢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51、60、84頁,及第89頁編者注6(指出福柯對材料的記憶有誤)。本文涉及譯文據原文有所改動(see Michel Foucault, «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 Paris: Gallimard/Seuil, 1997)。
[9] 詳見列寧《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一書的摘錄和批注》,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60卷),第82-108頁。
[10] 詳見卡爾·施米特《游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附識》,收入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增訂本)》,劉小楓編,劉宗坤、朱雁冰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9-190頁。
[11] 詳見列寧《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一書的摘錄和批注》,第85-98頁。
[12] See Jacques Lacan, «L’instance de la lettre dans l’inconscient ou la raison depuis Freud» ,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493-528.
[13] 福柯在《「必須保衛社會」》中也抨擊霍布斯的「戰爭狀態」「不是戰爭,而是表演的遊戲狀態」,是利用對戰爭的恐懼來構成與前述「歷史-政治話語」相對立的、在現代政治思想中佔統治地位的哲學-法律話語(詳見《必須保衛社會》,第92—104頁)。
[14] 在論述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時,施米特提及:「眾所周知,‘全民皆兵’也是組織抵抗拿破侖的戰爭的普魯士總參謀部職業軍官們的用語。克勞塞維茨便屬於這些軍官之列。」(卡爾·施米特《游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附識》,第195頁)
[15]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1頁。
[16]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6頁。
[17] 詳見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馮鋼、劉陽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16頁。
[18] 詳見桑德拉·哈爾珀琳《現代歐洲的戰爭與社會變遷:大轉型再探》,唐皇風、武小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6-10頁。
[19] 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社會》,第53頁。
[20]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p.60.
[21] See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p.ⅹⅹⅲ, p.37.
[22] 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Ⅰ, Torino, Einaudi editore, 1975, p.122. 後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簡稱「Quaderni」、卷數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所有引文均系本文作者從意大利文自譯。
[23] 列寧提出「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暴力手段>的繼續」(列寧《社會主義與戰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對戰爭的態度]》,第327頁)。
[24] 毛澤東所說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概括了兩者(詳見毛澤東《論持久戰》,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0頁)。
[25] 「政治鬥爭從‘機動戰’[按:葛蘭西在《獄中札記》里混用「運動戰(guerra di movimento)和」機動戰(guerra manovrata)兩種說法]轉變為‘陣地戰’……在歐洲,這種轉變發生於1848年之後,……1871年之後發生了同樣的轉變。」(Quaderni Ⅲ: 1768)「在政治史上,最後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按:指「運動戰」]就是1917年的那些事件,它們標誌著政治藝術與科學史的一個決定性轉折點。」(Quaderni Ⅲ: 1616)「在我看來,伊里奇懂得,必須把1917年在東方成功運用過的機動戰改變為在西方唯一可行的陣地戰……這就是我理解的統一戰線方案的含義……」(Quaderni Ⅱ: 866)
[26]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3卷),第893頁。
[27] 詳見佩里·安德森《葛蘭西的二律背反》,吳雙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7頁。後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簡稱「《葛》」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本文涉及譯文據原文有所改動(See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Verso, 2017)。
[28] 詳見伊曼努爾·康德《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啓蒙?》,收入李秋零編譯《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後的論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46頁;參見約翰·克里斯蒂安·勞爾森《顛覆性的康德:「公共的」和「公共性」的詞彙》,收入詹姆斯·施密特編《啓蒙運動與現代性:18世紀與20世紀的對話》,徐向東、盧華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9-276頁。
[29] 列寧寫道:「我們運動中的活動家所應當遵守的唯一嚴肅的組織原則是:嚴守秘密,極嚴格地選擇成員,培養職業革命家。」(列寧《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6卷],第134頁)
[30] 參見陳越《領導權與「高級文化」:再讀葛蘭西》,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年第5期,第30-37頁。
[31] 路易·阿爾都塞賦予哲學「論點」以「立場/陣地」(position)的意義,實際上使用了「陣地戰」話語來描繪「哲學戰場」上的理論鬥爭。他寫道:「‘陣地’一詞這裡重新出現在我們筆下並非偶然,因為這些陣地就是一些論點,而這些論點就是一些被佔領的陣地,包括對手的陣地……」「陣營並非一勞永逸地構成,陣地也不是一勞永逸地佔據。哲學是一場持續千年的塹壕戰……」(路易·阿爾都塞《在哲學中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吳子楓譯,北京出版社,2022年,第153、262頁)。
[32] 列寧《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一書的摘錄和批注》,第84頁。
[33] 詳見雅克·泰克西埃《馬克思恩格斯論革命與民主》,姜志輝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55-164、305-308頁。
[34] 詳見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37-542頁。
[35] 詳見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第545-546、541頁。
[36] 詳見路易·阿爾都塞《怎麼辦?》,陳越、張靖松、王寧泊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80-93頁;Louis Althusser, «Marx dans ses limites », in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Ⅰ , Paris: Stock/Imec, 1994, pp.502-505.
[37] 詳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0頁。
[38] 詳見路易·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收入路易·阿爾都塞《論再生產》,第453-459頁。
[39] 阿爾都塞寫道:「絕大部分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它們表面上是分散的)隸屬於私人領域。」(路易·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第455頁)
[40] 詳見伊曼努爾·康德《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啓蒙?》,第41頁。
[41] 伊曼努爾·康德《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收入李秋零編譯《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頁。
[42] 路易·阿爾都塞《馬基雅維利和我們》,收入陳越編譯《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4頁。
[43] 伊曼努爾·康德《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啓蒙?》,第41頁。譯文據原文有所改動(see Immanuel Kant, Werke: in sechs Bänden, Ⅵ, Wiesbaden: Insel Verlag, 1954, p.55)。
[44] 這也正是伊曼努爾·華勒斯坦在對十九世紀興起的三大政治意識形態(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進行歷史考察之後宣佈「1789年以來只有一種真正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的原因(詳見伊曼努爾·華勒斯坦《自由主義之後》,收入華勒斯坦等《自由主義的終結》,郝名瑋、張凡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89頁)。
[45] 原本是卡爾·施米特關於1813年4月普魯士戰事總動員令賦予人民游擊戰以正當性的說法(詳見卡爾·施米特《游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附識》,第185頁)。
[46] 詳見米歇爾·德·塞托《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方琳琳、黃春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9—104頁;吉爾·德勒茲和費利克斯·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輝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27—396頁;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p.79-93.
[47] 米歇爾·德·塞托《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第98頁。
[48] 吉爾·德勒茲和費利克斯·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331頁。譯文據原文有所改動(se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Mille plateaux, Paris: Minuit, 1980, p.440)。
[49] 詳見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35、42頁。
[50] 吉爾·德勒茲和費利克斯·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389頁。
[51]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pp.59-60.
[52] 安德森正確地指出:「在任何馬克思主義戰略中,把‘陣地戰’和‘運動戰’簡單對立起來,最終都變成了改良主義與冒險主義之間的對立。」(《葛》:108)
[53] Louis Althusser, « Soutenance d’Amiens », in Louis Althusser, Solitude de Machiavel et autre textes, Paris: PUF, 1998, p.205.
[54] 詳見列寧《論我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43卷),第373-374頁。
[55] 對葛蘭西「能動性」觀念的批判,詳見路易·阿爾都塞《怎麼辦?》,第64-66、75-77頁。
[56] Antonio Gramsci, « 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 », in David Forgacs, ed, The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5.
[57] 列寧《論我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第374頁。
[58] 詳見托·斯·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論文》,卞之琳、李賦寧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4-5頁。
[59] 列寧《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43卷),第394頁。
[60] 阿爾都塞曾針對「‘最薄弱環節’這個列寧主義主題」做出論述(詳見路易·阿爾都塞《矛盾與過度決定(研究筆記)》,收入《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82頁。譯文據原文有所改動[See Louis Althusser, « Contradiction et surdetermination », in Louis Althusser, Pour Marx,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65, p.92])。
[61] 列寧《論合作社》,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43卷),第371-372頁。
[62] 葛蘭西寫道:「現代君主必須而且必然是知識與道德改革的倡導者和組織者,這意味著它要為民族人民的集體意志在今後的發展,為實現更高更完整的現代文明形式奠定基礎。」(Quaderni Ⅲ: 1560)
[63] 列寧《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第3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