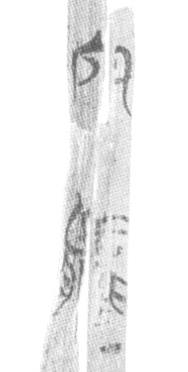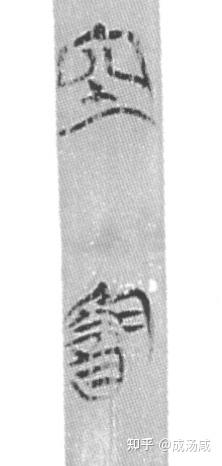周代楚国国君的姓是「芈」、「熊」、「楚」还是「酓」?
姓「芈」还是姓「熊」本质是一回事,因为「熊」在古楚语的读音就是「芈(me)」,所以「熊」是意译,「芈」是音译。就像国外姓「White」的,有人用音译就翻译为「怀特」,有人直接意译就是姓「白」,都一样。 但后来「熊」和「芈」在和周人的交流使用中又出现了分化:「熊」变成了楚人的「氏」,「芈」变成了楚人的「姓」。所以一定要问楚人的「姓」是什么,那姓「芈」。 〇.楚人的熊崇拜 楚人应该是有熊崇拜的。我们在战国楚简里看到楚人祭祀有三位先祖:老童、祝融、穴熊,这三位的神话色彩都很强,祝融大家认识就不多说了,这个老童是祝融他爹[1],穴熊则和《山海经》里的熊山神人有关: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山海经》 穴熊的形象最初应该就是一只栖息在熊山洞穴里的神熊,楚人把它当自己的部族的神,后来穴熊的形象逐渐人格化,就变成楚人的祖先了。另外楚帛书里还有「大熊伏羲」的记载,似乎在楚人的认识里,伏羲也是熊的形象。 楚国国君名字都叫「熊 X」,应该就是源自楚人的熊崇拜,他们自认是穴熊的后人,所以名字里都带「熊」。 附带说一下,《史记》里楚人先祖谱系记载比较混乱。《史记》说楚国的始祖是季连,季连的孙子是穴熊,而穴熊的后人是鬻熊。但从出土楚简的祭祀记载来看,穴熊和鬻熊应该同是一个人,这个已无疑议,但穴熊为什么能写作鬻熊则不清楚;另外按《清华简·楚居》的说法,季连和穴熊好像也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史记》里这么多代人其实都是同一个人的马甲。 一.「芈」音译、「熊」意译 话归正题,来说「熊」和「芈」的关系。 古楚语有一些汉语没有的词汇,许多是受侗台语的影响。古楚语的「熊」应该就读「me」这个音,汉人用「芈」字来音译。 现在的侗语称「熊」为「me」,泰语称「熊」为「mi」,还有西南很多民族对熊的称呼都是类似的发音,都是同一个词的孑遗。 简单来说:「芈」是音译,「熊」是意译。 所以「熊」和「芈」本质是一回事,就是楚人自己的族氏。 p.s. 据 @Mustafa Xia 说:参考原始台语(Proto-Tai, PT)*ʰmwɯjᴬ “熊”,原始南岛语(Proto-Austronesian, PAN) *tsumaj “熊”。按照 Smith(2022),PAN *C1v1C2v2C3 > PT *(C1)C2v1v2C3,所以 PAN *tsumaj > *C.mwaj > PT *ʰmwɯjᴬ是规则对应。当然楚国王室说的仡台语可能未必是台语,所以这一 metathesis 有没有发生也未可知。 二.楚人姓氏分化 但后来「熊」和「芈」在使用中出现了分化:「熊」变成了楚人的「氏」,「芈」变成了楚人的「姓」,就又不是一回事了。 周人的「姓」和「氏」是不一样的东西。周人男子称「氏」,用来区别身份地位;女子称「姓」,用来区别部族。这个很好理解:男子都生活在同一个部族里,当然都是同姓的,所以称姓没有意义,只有称呼部族里的职位、居住地等信息,才能起到区别的作用,这些信息就是「氏」。而女子是要出嫁到别的部族的,女子称姓,人家才能知道是哪个部族嫁过来的。 区分「姓」和「氏」,这是周人的习惯,楚人本来未必有这样的分别。但楚人后来跟着周人混,文化交融后,楚人也得有自己的「姓」和「氏」了,不然老大哥不带你玩。 于是楚人用音译的「芈」作为自己部族的姓,把意译的「熊」作为自己部族的氏。所以文献中楚国的女子都叫「X 芈」,楚国的君主都叫「熊 X」。 不过在出土文献里,楚国女子也有姓放前面叫「芈 X」的,并不符合周人女子姓放后面的规则。说明楚人有时候也不太严格依照周人那套来,还是有自己的习惯,和男子叫「熊 X」保持一致。 三.出土所见楚人姓氏 「芈」和「熊」是传世文献里的写法,现在出土文献里的用字则又有不同。 芈 - 嬭 「芈」在出土铜器上写作「嬭」,「嬭」应该是标准写法,加女字旁是为了强调「姓」是女子用的。 「芈」是「嬭」的同音字,可能因为比「嬭」好写,后来反而成为主流了,所以《左传》里都用的「芈」字。 熊 - 酓 在出土的楚国竹简里,很多楚国君主名里的「熊」都写作「酓」[2]。 「熊」和「酓」在先秦是音近字,有可能是楚人在从蛮夷逐渐变文化人的过程中,觉得「熊」太野蛮,有意改用了更中性的「酓」。 但严格来说「熊」和「酓」的读音没那么接近,可能是因为和熊同音的字过少,所以只能借用一个不那么音近的音近字。楚简里书写楚人先祖穴熊,「穴熊」和「穴酓」两种写法都有,说明对于当时的楚人来说,「熊」和「酓」是能相互替换的。 穴熊(葛陵简) 穴酓(葛陵简) 查看知乎讨论


姓「芈」还是姓「熊」本质是一回事,因为「熊」在古楚语的读音就是「芈(me)」,所以「熊」是意译,「芈」是音译。就像国外姓「White」的,有人用音译就翻译为「怀特」,有人直接意译就是姓「白」,都一样。
但后来「熊」和「芈」在和周人的交流使用中又出现了分化:「熊」变成了楚人的「氏」,「芈」变成了楚人的「姓」。所以一定要问楚人的「姓」是什么,那姓「芈」。
〇.楚人的熊崇拜
楚人应该是有熊崇拜的。我们在战国楚简里看到楚人祭祀有三位先祖:老童、祝融、穴熊,这三位的神话色彩都很强,祝融大家认识就不多说了,这个老童是祝融他爹[1],穴熊则和《山海经》里的熊山神人有关: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山海经》
穴熊的形象最初应该就是一只栖息在熊山洞穴里的神熊,楚人把它当自己的部族的神,后来穴熊的形象逐渐人格化,就变成楚人的祖先了。另外楚帛书里还有「大熊伏羲」的记载,似乎在楚人的认识里,伏羲也是熊的形象。
楚国国君名字都叫「熊 X」,应该就是源自楚人的熊崇拜,他们自认是穴熊的后人,所以名字里都带「熊」。
附带说一下,《史记》里楚人先祖谱系记载比较混乱。《史记》说楚国的始祖是季连,季连的孙子是穴熊,而穴熊的后人是鬻熊。但从出土楚简的祭祀记载来看,穴熊和鬻熊应该同是一个人,这个已无疑议,但穴熊为什么能写作鬻熊则不清楚;另外按《清华简·楚居》的说法,季连和穴熊好像也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史记》里这么多代人其实都是同一个人的马甲。
一.「芈」音译、「熊」意译
话归正题,来说「熊」和「芈」的关系。
古楚语有一些汉语没有的词汇,许多是受侗台语的影响。古楚语的「熊」应该就读「me」这个音,汉人用「芈」字来音译。
现在的侗语称「熊」为「me」,泰语称「熊」为「mi」,还有西南很多民族对熊的称呼都是类似的发音,都是同一个词的孑遗。
简单来说:「芈」是音译,「熊」是意译。
所以「熊」和「芈」本质是一回事,就是楚人自己的族氏。
p.s. 据 @Mustafa Xia 说:参考原始台语(Proto-Tai, PT)*ʰmwɯjᴬ “熊”,原始南岛语(Proto-Austronesian, PAN) *tsumaj “熊”。按照 Smith(2022),PAN *C1v1C2v2C3 > PT *(C1)C2v1v2C3,所以 PAN *tsumaj > *C.mwaj > PT *ʰmwɯjᴬ是规则对应。当然楚国王室说的仡台语可能未必是台语,所以这一 metathesis 有没有发生也未可知。
二.楚人姓氏分化
但后来「熊」和「芈」在使用中出现了分化:「熊」变成了楚人的「氏」,「芈」变成了楚人的「姓」,就又不是一回事了。
周人的「姓」和「氏」是不一样的东西。周人男子称「氏」,用来区别身份地位;女子称「姓」,用来区别部族。这个很好理解:男子都生活在同一个部族里,当然都是同姓的,所以称姓没有意义,只有称呼部族里的职位、居住地等信息,才能起到区别的作用,这些信息就是「氏」。而女子是要出嫁到别的部族的,女子称姓,人家才能知道是哪个部族嫁过来的。
区分「姓」和「氏」,这是周人的习惯,楚人本来未必有这样的分别。但楚人后来跟着周人混,文化交融后,楚人也得有自己的「姓」和「氏」了,不然老大哥不带你玩。
于是楚人用音译的「芈」作为自己部族的姓,把意译的「熊」作为自己部族的氏。所以文献中楚国的女子都叫「X 芈」,楚国的君主都叫「熊 X」。
不过在出土文献里,楚国女子也有姓放前面叫「芈 X」的,并不符合周人女子姓放后面的规则。说明楚人有时候也不太严格依照周人那套来,还是有自己的习惯,和男子叫「熊 X」保持一致。
三.出土所见楚人姓氏
「芈」和「熊」是传世文献里的写法,现在出土文献里的用字则又有不同。
芈 - 嬭
「芈」在出土铜器上写作「嬭」,「嬭」应该是标准写法,加女字旁是为了强调「姓」是女子用的。
「芈」是「嬭」的同音字,可能因为比「嬭」好写,后来反而成为主流了,所以《左传》里都用的「芈」字。
熊 - 酓
在出土的楚国竹简里,很多楚国君主名里的「熊」都写作「酓」[2]。
「熊」和「酓」在先秦是音近字,有可能是楚人在从蛮夷逐渐变文化人的过程中,觉得「熊」太野蛮,有意改用了更中性的「酓」。
但严格来说「熊」和「酓」的读音没那么接近,可能是因为和熊同音的字过少,所以只能借用一个不那么音近的音近字。楚简里书写楚人先祖穴熊,「穴熊」和「穴酓」两种写法都有,说明对于当时的楚人来说,「熊」和「酓」是能相互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