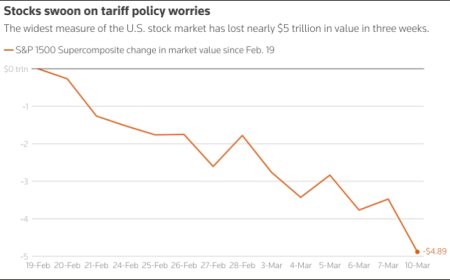一针70万的救命药砍到3.3万,这不是一个“拍脑门的结果”
编者按: 在大健康视域下,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现民众合理就医,解决民众就医难、就医贵的问题乃当务之急。 网易财经智库邀请到了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围绕“大健康与医保制度”深入探讨,厘清健康产业、医药创新、健康人力资本等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机制,并对现存的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文/刘国恩】 呼吁试点按照居民健康程度来支付医疗服务的新医疗卫生体制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未来在两个方面可以做更多工作。一是如何更有效地完善支付手段。因为现在的医疗服务是通过医疗保险第三方去购买的,发挥了政府筹资的作用,又发挥了市场作为购买方的作用。 但是作为第三方去购买服务的时候,如何能够让医保方、患者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激励能够越来越相容,达到的目的才是最佳的。假设我们继续沿用现在的做法,中国也好,很多其他国家也好,都是按照疾病来进行支付的。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住院费用通常来说会高于门诊费用,作为医疗服务提供机构,当然希望住院的人越多越好;但从医保方和患者方的角度来说,个人当然不愿意得大病,医保那边还要支出更多的钱。因此,医保方、患者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如果这个激励不相容,各方就会在矛盾中前行。 假设我们能够探讨一个更有效的方式,能够按照居民的健康程度来支付我们的医疗服务——提供服务的主体生的病越少,医保给这些主体支付的越多;生的病越多,则要从我们给的支付里面扣除。这样医疗服务提供方才有动力和积极性来开展预防性的服务,开展促进健康的服务,因为这样做它们才可以留下更多的钱。这样的结果是,医疗服务提供方希望患者少生病,这和患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医保方作为支付机构也没有增加额外的支出,从而使得三方的激励相容。 医保办工作人员(右)向前来咨询药品报销问题的居民讲解相关政策。 资料图:新华社 以健康为基础的支付方式,目前当然只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如何做得到我们并不清楚。但中国这么大,我们是否可以在一些地方进行试验呢?可以和医院签订合同,医保给它们进行结算的时候,不是按照患者看了多少次病,而是看这个地方的居民健康水平。居民健康水平越高,给医院结算的收入越高,反之则扣除部分收入,医院留下的收入就会减少。这样,医疗服务机构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就能够相容。这个理论上讲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实践起来肯定有难度,但是它不影响我们去做实验。 第二,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如何发挥个人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的作用,而不要通过完全家长式的管理思路,替人们把所有的健康医疗决策都做完。这样可能会花更多的经费,还不会得到每一个人特别好的配合。所以应该把行为经济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更好地考虑到我们未来卫生政策的制定当中,从而让每个人发挥越来越多的能动性,使得他们身心愉快,配合程度更高。 真实的医保谈判揭秘:70万的保命药如何降价到3.3万? 对医药的创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产权的保护。对医药创新的产权当然就体现在它的专利保护上。根据全球通行的原则,专利周期是20年左右。 专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进行创新本身是高度不确定的一项工作,它的投入很大,研发周期很长。以医药创新的数据来看,美国一个创新药物从获得投资到成功上市,平均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并且它的投资的力度大概在20亿美元左右。中国药企在新药创新方面,时间成本与美国药企差不多,投资的规模大概是2亿多美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药的研发和上市,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一旦它成功研发出来并且上市以后,社会当然就要给它一定的保护,为它的投入得到合理的回报给出相应的支持,同时也激励这些研发的主体,能够继续从事医药的研发工作。专利保护的本质是保护它可以自由定价,获得更好回报,这个核心是最重要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19年的时候,中国上市了一款特别有名的药物,商业名叫诺西那生钠,它是治疗脊髓肌肉萎缩症的药。脊髓肌肉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病,主要是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基本上小孩子就站不起来,大多数会面临死亡,2019年之前没有药物可治。2019年该药上市以后,打一针是70万人民币左右,大概第一年治疗要六针。如果按照70万一针计算,第一年就是420万。 2021年,这个药物的厂商就通过国家医保局年度药物目录的更新调整平台,提请考虑进入国家医保,可以给一个医保谈判的价格出来。最后这个药物,从70万元谈到了3.3万元一支,史称“灵魂砍价”。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降幅。社会上对这个降幅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有正面的,站在患者的角度,站在医保的角度。也有一些负面的说法,站在新药物企业的角度,担心对创新支持力度可能不够,利润不够。 2021国家医保目录药品谈判,医保局谈判代表张劲妮将曾经“70万一针”的罕见病救命药,最终以每瓶3.3万元的价格纳入医保。 我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事实上从70万元降到3.3万元,并不是这些所谓的医保部门的相关人员或者专家拍脑门儿,给的3.3万元,它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并且这个谈判并不是完全没有科学基础。我直接参与了相关工作,国家医保局在2018年就启动了系统的国家医保目录更新调整工作,请了三个专家组来对这些药物进行评价。 第一个是临床专家组,其中包括临床的大夫,临床研究人员,还有药剂师等等,他们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们给予的评估基础就是临床上是否必需,即临床上有没有这样的同类药物,或者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药物,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来判断临床是否必需。 第二个组是经济学专家。他们基于经济学的原则来评估这些药物,看这个药物应用到患者身上,它给患者带来多大的健康收益,以及医保因此要付出多少钱。他们来算经济账,是否值得,然后给一个相应的价格。 第三个组是基金测算组,更多的是来自地方政府管理医保基金的专业人员。他们做的工作的重点是,如果一个新的药品纳入到国家医保目录以后,各个地方的医保基金能不能够支付得起。所以他们的工作是算钱够不够,经济学组算值还是不值,临床专家算必要还是不必要。三个工作组分工非常明确,并且相互不见面不交流,形成独立的专家意见,再综合起来,交给有关的管理部门,形成所谓信封里的那个价格,直到谈判的最后一关,谈判组和企业进行谈判时,他们几个专家才第一次打开信封,全流程都是有人监督的,不能违规。 经济学谈一个东西的价格,更多还是基于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它的成本。诺西那生钠来来回回大概谈了八九轮,最后谈到3.3万元一支。我这里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3.3万元不是完全离谱的一个价格,更不是一个拍脑门的结果。因为在目前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标识上面,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不成文的、大家都遵守的标准,关于一个新的医药技术,它如果应用到患者身上,能够延长一年的寿命,只要不超过这个患者所在国家人均收入的三倍,就属于一个值得购买的、可以被推荐的医药技术。

编者按:
在大健康视域下,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现民众合理就医,解决民众就医难、就医贵的问题乃当务之急。
网易财经智库邀请到了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围绕“大健康与医保制度”深入探讨,厘清健康产业、医药创新、健康人力资本等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机制,并对现存的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文/刘国恩】
呼吁试点按照居民健康程度来支付医疗服务的新医疗卫生体制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未来在两个方面可以做更多工作。一是如何更有效地完善支付手段。因为现在的医疗服务是通过医疗保险第三方去购买的,发挥了政府筹资的作用,又发挥了市场作为购买方的作用。
但是作为第三方去购买服务的时候,如何能够让医保方、患者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激励能够越来越相容,达到的目的才是最佳的。假设我们继续沿用现在的做法,中国也好,很多其他国家也好,都是按照疾病来进行支付的。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住院费用通常来说会高于门诊费用,作为医疗服务提供机构,当然希望住院的人越多越好;但从医保方和患者方的角度来说,个人当然不愿意得大病,医保那边还要支出更多的钱。因此,医保方、患者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如果这个激励不相容,各方就会在矛盾中前行。
假设我们能够探讨一个更有效的方式,能够按照居民的健康程度来支付我们的医疗服务——提供服务的主体生的病越少,医保给这些主体支付的越多;生的病越多,则要从我们给的支付里面扣除。这样医疗服务提供方才有动力和积极性来开展预防性的服务,开展促进健康的服务,因为这样做它们才可以留下更多的钱。这样的结果是,医疗服务提供方希望患者少生病,这和患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医保方作为支付机构也没有增加额外的支出,从而使得三方的激励相容。

医保办工作人员(右)向前来咨询药品报销问题的居民讲解相关政策。 资料图:新华社
以健康为基础的支付方式,目前当然只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如何做得到我们并不清楚。但中国这么大,我们是否可以在一些地方进行试验呢?可以和医院签订合同,医保给它们进行结算的时候,不是按照患者看了多少次病,而是看这个地方的居民健康水平。居民健康水平越高,给医院结算的收入越高,反之则扣除部分收入,医院留下的收入就会减少。这样,医疗服务机构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就能够相容。这个理论上讲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实践起来肯定有难度,但是它不影响我们去做实验。
第二,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如何发挥个人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的作用,而不要通过完全家长式的管理思路,替人们把所有的健康医疗决策都做完。这样可能会花更多的经费,还不会得到每一个人特别好的配合。所以应该把行为经济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更好地考虑到我们未来卫生政策的制定当中,从而让每个人发挥越来越多的能动性,使得他们身心愉快,配合程度更高。
真实的医保谈判揭秘:70万的保命药如何降价到3.3万?
对医药的创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产权的保护。对医药创新的产权当然就体现在它的专利保护上。根据全球通行的原则,专利周期是20年左右。
专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进行创新本身是高度不确定的一项工作,它的投入很大,研发周期很长。以医药创新的数据来看,美国一个创新药物从获得投资到成功上市,平均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并且它的投资的力度大概在20亿美元左右。中国药企在新药创新方面,时间成本与美国药企差不多,投资的规模大概是2亿多美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药的研发和上市,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一旦它成功研发出来并且上市以后,社会当然就要给它一定的保护,为它的投入得到合理的回报给出相应的支持,同时也激励这些研发的主体,能够继续从事医药的研发工作。专利保护的本质是保护它可以自由定价,获得更好回报,这个核心是最重要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19年的时候,中国上市了一款特别有名的药物,商业名叫诺西那生钠,它是治疗脊髓肌肉萎缩症的药。脊髓肌肉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病,主要是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基本上小孩子就站不起来,大多数会面临死亡,2019年之前没有药物可治。2019年该药上市以后,打一针是70万人民币左右,大概第一年治疗要六针。如果按照70万一针计算,第一年就是420万。
2021年,这个药物的厂商就通过国家医保局年度药物目录的更新调整平台,提请考虑进入国家医保,可以给一个医保谈判的价格出来。最后这个药物,从70万元谈到了3.3万元一支,史称“灵魂砍价”。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降幅。社会上对这个降幅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有正面的,站在患者的角度,站在医保的角度。也有一些负面的说法,站在新药物企业的角度,担心对创新支持力度可能不够,利润不够。

2021国家医保目录药品谈判,医保局谈判代表张劲妮将曾经“70万一针”的罕见病救命药,最终以每瓶3.3万元的价格纳入医保。
我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事实上从70万元降到3.3万元,并不是这些所谓的医保部门的相关人员或者专家拍脑门儿,给的3.3万元,它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并且这个谈判并不是完全没有科学基础。我直接参与了相关工作,国家医保局在2018年就启动了系统的国家医保目录更新调整工作,请了三个专家组来对这些药物进行评价。
第一个是临床专家组,其中包括临床的大夫,临床研究人员,还有药剂师等等,他们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们给予的评估基础就是临床上是否必需,即临床上有没有这样的同类药物,或者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药物,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来判断临床是否必需。
第二个组是经济学专家。他们基于经济学的原则来评估这些药物,看这个药物应用到患者身上,它给患者带来多大的健康收益,以及医保因此要付出多少钱。他们来算经济账,是否值得,然后给一个相应的价格。
第三个组是基金测算组,更多的是来自地方政府管理医保基金的专业人员。他们做的工作的重点是,如果一个新的药品纳入到国家医保目录以后,各个地方的医保基金能不能够支付得起。所以他们的工作是算钱够不够,经济学组算值还是不值,临床专家算必要还是不必要。三个工作组分工非常明确,并且相互不见面不交流,形成独立的专家意见,再综合起来,交给有关的管理部门,形成所谓信封里的那个价格,直到谈判的最后一关,谈判组和企业进行谈判时,他们几个专家才第一次打开信封,全流程都是有人监督的,不能违规。
经济学谈一个东西的价格,更多还是基于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它的成本。诺西那生钠来来回回大概谈了八九轮,最后谈到3.3万元一支。我这里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3.3万元不是完全离谱的一个价格,更不是一个拍脑门的结果。因为在目前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标识上面,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不成文的、大家都遵守的标准,关于一个新的医药技术,它如果应用到患者身上,能够延长一年的寿命,只要不超过这个患者所在国家人均收入的三倍,就属于一个值得购买的、可以被推荐的医药技术。